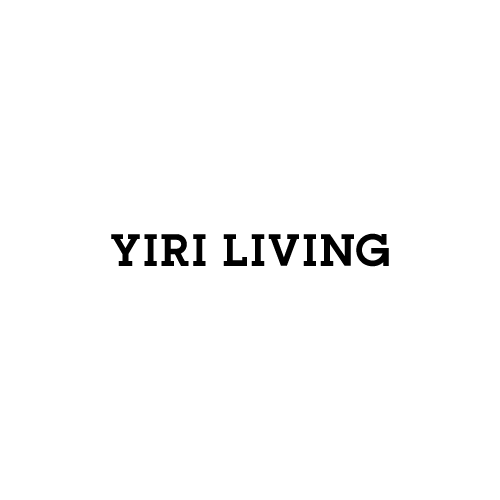植覺禮 X 影評人馬欣
植覺訪談Ⅰ_一個人的幸福感_花卉篇
花季將至未至時
整日天灰,向晚未到,涼雨已先染深泥牆。
木桌上的小燈暖黃,細霧嬝嬝的黑咖啡溫燙。還未切入正題,摟著抱枕,一派怡然的馬欣已侃侃聊起關於「花」的聯翩情懷。她說,「人若沒有花季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。」人不是塑膠花,不會也不必始終盛放,但至少要有過一次燦爛的開與落。沒有花季便無法詮釋自己,違反生命本質,人的疲勞憂傷、恐慌焦慮皆由於此。
在無限與有限之間
熱愛電影的馬欣,從小內心就完整運行著一座宇宙。成長期,父母皆忙於事業,相差十二歲的兄姐有自己的社交生活,獨處於是成為她的日常。就學以前,小女孩蜷窩在屋梯轉角處,像坐在太空船駕駛艙裡,邊窗暈染進來午後四點的斜陽,在眼底反映如星系與星系間熠熠的寂靜光年。上學後,她像個訊號零格,斷線的太空人,自閉症的嫌疑糾纏不休。入職場,終學會隨時自在享受一個人的狀態。她說起,有次在公司露台放鬆一支菸的時間,當下不見同事或主管,沒有人,她獨自坐在小紅椅上,黃昏霞色正絢麗 ⋯⋯ 啊,那一刻真是天堂般的幸福!
對馬欣來說,獨處自幼便根生為本能,既是本能就沒有好與不好的糾葛。一如植物不會嫌棄滋育自己的泥土。但對多數人而言,處在社群網絡的時代,一個人,似乎等於生活與自我價值的全面潰敗。「人最大的快樂在於從有限裡面發現自己的無限,而不是從別人的無限裡發現自己的有限。」現代人痛苦的來源,最大的文明病,無非就是發現別人的無限,而相對地每天在提醒自己的有限。
「電影中,是否有即便是一個人也充滿幸福感的角色?」我好奇地問熟悉電影的馬欣。
她不假思索,「海上鋼琴師,1900。」他終其一生沒有下船。或許,他曾痴戀一個乘船的美麗女孩;也曾站在郵輪舷梯上,望著紐約那座大城市遲疑,但終究毅然返身回到船艙的舷窗旁、熟悉的鋼琴前。他對朋友說,他看不到盡頭。比起紐約無盡的有限,他可以在黑白鍵(有限)裡開發自己的無限,那樣的快樂會每一天遞增。他懂得自己之於紐約什麼也不是,相反的,船上的鋼琴之於他是安適幸福的,是無可取代的生命意義。
盡在不言中的幸福感
我問,那個在寫作裡向來眼冷心熱的馬欣會選什麼花卉形容自己?「有好幾次,我因為七里香感到幸福。台北的夏天又悶又濕很不舒服。但有時候經過公園,一陣七里香氣輕易就驅散了暑溽,悶熱被消滅許多。那一刻像被施了魔法,獨處的氛圍忽然立體起來,就像與朋友說再見後,一個人坐下來,緩一緩,不急著做什麼,只有我跟飄逸的花香存在那個周遭全都靜下來的環境裡。」她綿軟清甜的聲線,如此悠悠緩緩地傾訴了心裡親愛的七里香。她不要被詩歌頌揚,也不要盛開時節動京城的,不要濫情的,強烈存在感的花。只要如那七里香,遠遠聞香,卻不一定記得花貌,某一處,偶然一時,乍然芬芳。
坐在公園裡,聞著七里香獨處時,她習慣也喜歡看人。就像看電影時,她是專業的影評人,也純粹是一個觀眾。她觀察,讀他們的細節,解他們的線索。「當一個觀眾幸福的是,慢慢的,你看人會變得溫柔,不帶成見地看就不會憤世嫉俗,那個溫柔的你會饒過自己,無關乎別人遭遇狀態的好壞,而是你知道所有人都很辛苦地活著。」
馬欣形容自己如暗暗芬芳的七里香,同時也詮釋了屬於她一個人的幸福感的狀態。本以為那就是她的註解了,她卻繼續有感而發地,「幸福應該單屬於個人,某一時的限定,甚至沒有人知道。說不出來那為什麼是幸福,才是幸福。能說出理由的時候,就不算幸福,甚至虧待了它,之後再說起那個幸福,終究不會圓滿。」
原來一個人的幸福感也彷若花季中一株將綻未綻的花苞,那欲語還休的片刻一瞬,恆美。

馬欣
影評人,作家。曾擔任娛樂線採訪與編輯工作二十多年,目前從事專欄文字的筆耕。著有《反派的力量》、《當代寂寞考》、《長夜之光》與《階級病院》。
-
更多「馬欣」請參考 馬欣粉絲專頁、痞客邦部落格
-
更多「植覺禮」請參考」 a better day 伊日好生活